推开“房间”的门:一部“生命存在的舞台” 史
“二战”结束以后,法国史学,尤其是年鉴-新史学在国际史坛声名显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长期引领战后西方史学发展潮流。其间,法国女性史坛高手当然也常有出现。在足以显示“巾帼不让须眉”的这些人中,出于习史经历和研究旨趣,本人尤为欣赏和推崇的是犹如“双子星座”的莫娜·奥祖夫和米歇尔·佩罗。这两人,前者早年以研究法国第三共和国小学教师蜚声史坛,随即更多以法国大革命史专家闻名遐迩;后者先以对19世纪法国工人的研究崭露头角,继而转向在妇女史等领域大显身手。人们只要知晓她们二人分别携手孚雷、杜比级别的史坛巨擘,主编了《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西方妇女史》之类的里程碑式著作,就不难掂量出她们在法国乃至国际史学界该占有的地位。

米歇尔·佩罗
尽管在我心目中两人同等出色,但佩罗较之奥祖夫确实更易让我产生亲近感。这显然与我早年遇到的法国“贵人”有关。此人就是时任巴黎八大教授的克洛德·维拉尔(Claude Willard)。维拉尔与佩罗一样,也是拉布鲁斯,即那位与布罗代尔齐名的战后法国史坛泰斗的高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本人初涉法国人民阵线运动史时,先是有幸受到来杭讲学的维拉尔教授指点,接着在他的邀请和帮助下首次赴法,在巴黎八大进修近现代法国社会史。进修期间,维拉尔教授既在生活和学习上对我关爱有加,还设法为我提供求教于社会史名家的机会,当中自然有可以见到佩罗的学术活动。可以说,正是这些机缘令我不仅早就开始关注佩罗,此后也一直对她青睐有加。2009年,《私人生活空间史》这本佩罗自己用力甚勤,广大读者期盼已久的著作终于出版了。无疑,这也是1928年出生的佩罗晚年最让我意外,同时也更添好感之事。
《私人生活空间史》出版后在法国好评如潮,还获得过重要奖项。因此,本人早就关注此书,同时还期望值颇高。事实上,早想“一睹为快”的我,在出版社约我翻译并寄来法文版时不仅爽快答应,更是书一到手就打开阅读。在读过之后,我不仅觉得它丝毫没有让我失望,而且再次激起了对作者的敬意。这种敬意的油然而生,固然与佩罗和家父年龄相仿有些关系,也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就此,本人以为,本书能取得如此成功,除视角独特、充满新意、洞见迭出,至关重要的是,佩罗力求将“房间”当作“生命存在的舞台”来书写历史,其间还着力体现了有良知、有担当的优秀史家须有的一大特点,即乐于和善于展示他(或她)本人的(社会)“介入”;同时,她也让自己兼具的才情、激情和温情各得其所,淋漓尽致地在字里行间得到体现。
《私人生活空间史》一书,写作视角之新奇独特,实可一目了然。尽管如此,作者落笔时具有的关照、秉持的理念,仍有必要先予以审视和揭示。就此,本人特别想指出一点,佩罗不仅视“房间”为“生命存在的舞台”,且在着手书写房间史时早就别具慧眼地看到:“作为这个世界的基本粒子,房间的秩序揭示了世界的秩序。”唯其如此,她在序言中开宗明义:“从临盆到临终,房间是生命存在的舞台,至少是剧场的后台。在这里,面具被摘下,衣装被脱下,躯体完全沉溺于情绪、悲伤、感性。人们会在这里度过人生的近半时间,一段属于肉体、昏昏沉沉、沉浸于黑夜的时光,一段时而失眠、胡思乱想、梦魇缠绕的时光。这是一扇通往无意识,甚至通往彼世的窗户;半明半暗增添了房间的魅力。”
才情激荡,可谓佩罗于此书首先带给我的强烈印象。这位史学家在书写过程中自然流露的深厚文学素养,更是令我折服。对此,人们甚至不妨如是断言,如果说《小说鉴史》是史学名家奥祖夫具有非凡文学造诣的明证,那么佩罗凭借本书,在文学才情上完全可和奥祖夫这位她相识多年、惺惺相惜的闺蜜媲美。关于佩罗的文学才情,篇幅所限,难以更多介绍和探讨,只能暂时满足于先在此特别强调,佩罗在写本书时,非但将有关小说视若“取之不竭的资源”,同时还充满洞见地指出,“在19世纪,小说赋予私人空间——上流社会和家庭情景剧——巨大的重要性”。还值得关注的是,佩罗书中的很多描述是如此富有感染力和别具一格,就连作为法国年鉴-新史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之一的安德烈·比尔吉埃尔也叹为观止,这位享誉国际史坛的历史人类学家在为本书撰写的书评中挥笔写道:“本书像自然缀连起的一幕幕话剧,让读者欲罢不能。”随后,他在提及此书“追述了来自时光裹挟下各色人等的记忆,他们当时的情绪以及想法”时,还令人印象深刻地夸赞作者具有“普鲁斯特一般的笔触”。
激情充沛,是佩罗在本书中给人留下的又一突出印象。坦率地讲,本人此前对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史的探讨,让我更容易去体察这些激情何以产生。而佩罗今年岁首出版的《以女历史学家的身份介入》中的“夫子自道”,显然也更利于帮助我去感受与追踪她这代“介入型”史学家的治史旨趣和思想轨迹。实难否认,佩罗和她同时代的不少优秀史家一样,绝非只是“为稻粱谋”走上治史道路,而是一直有社会责任感或家国情怀在驱动。正是有了类似驱动,佩罗从最早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相继投入了1968年“五月风暴”以及倡导监狱改革、提升妇女地位等各种重大社会政治运动。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在以一位优秀女性史学家的特有方式进行“介入”,即以系统扎实、新意迭出的史学成果作为“理解时世的工具和现实介入的手段”。如果说佩罗早年对工人运动史,后来对妇女史的研究均属此列,那么,晚年的她被“房间这个小宇宙”及其具有的政治维度强烈吸引,又何尝不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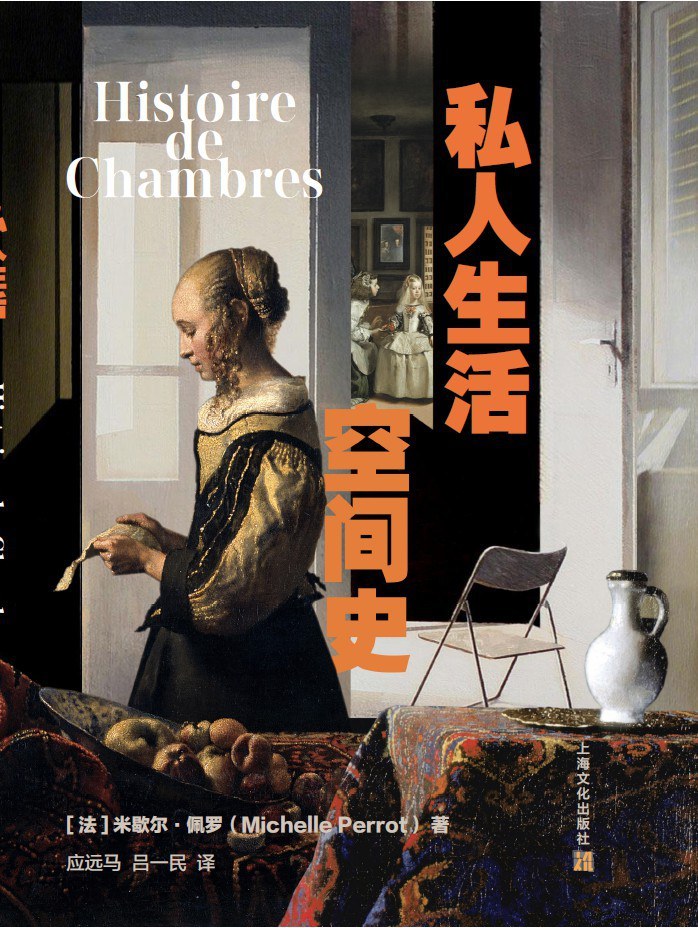
《私人生活空间史》,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将出版
温情洋溢,不啻佩罗在《私人生活空间史》字里行间给人带来的强烈感受。历史学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学问,当坚持以人为中心,并以关心人,特别是芸芸众生过往和当下的命运为要务。在这点上,佩罗的表现一贯出色。更触动我的是,佩罗的家境实际上向来不错,而且据她自己在《以女历史学家的身份介入》中的说法,她在家中或工作中与之相处的大多数男性对她也都相当好,但就是这样一位史学家,却一直对普罗大众,尤其是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工人和妇女充满关切、具有温情。为此,她年轻时就投身于研究19世纪法国工人状况、第三共和国前期的工人罢工;人到中年后又转向拓展妇女史的研究。即便于年届八旬出版的本书中,佩罗也依然“痴心不改”,给予女性包括女工诸多篇幅,同时赋予她们丰富而独特的地位。
2024年2月,佩罗《以女历史学家的身份介入》新书发布会在巴黎举行。在巴黎的学友为我代买此书并帮我获得佩罗的题赠与签名后,第一时间把新书送到我手里。此书确实只是本小册子,篇幅不大却内容颇丰。读完堪称“自我史学”典范之作的此书后,我对这位属于我父母辈、至今仍活力四射的资深学者更是充满敬意。同时,对佩罗撰写“房间史”的良苦用心非但有了更多“同情理解”,还进一步认识到佩罗等人终其一生的“介入”,其实不过属于力求以自身独特方式,让包括“房间”在内的各种“生命存在的舞台”,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呈现出各自该有的,即更符合人性多种需求的样貌。当然,在读过佩罗晚年出版的相关著作后,对当代法国史学名家长期保持活力的原因,本人亦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体认,在盛极而衰的年鉴—新史学派于20世纪90年代迎来“批判转向”后,这些史学家坚持让法国“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日益凸显其反思性、包容性、创新性、现实性、公众性。
凡此种种,本人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感慨之余,本人不由得想起了我的法国“贵人”给我的见面礼——一盒磁带。这盒磁带在他人眼里确实毫不起眼,但对正研习法国人民阵线运动史的我来说却弥足珍贵。因为,它是1986年法国纪念人民阵线运动50周年时,维拉尔教授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史权威参与的访谈节目录音。一想到这里,我的耳畔就会响起一个法语单词——Carrefour。诚然,Carrefour时下更多是以“家乐福”为我们知晓,但在节目录音中作为访谈栏目名称,由浑厚的男中音伴随富有冲击力的背景音乐反复念出的这个单词,其本义却主要还是“十字路口”。我不免还想到,如果说人民阵线运动事关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道路选择,那么,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人类又何尝不是在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上面临着重大抉择。
当今之世,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和令人担忧的趋势越来越多地出现。因而,年鉴学派两大创始人之一布洛赫的忠告,“对现实的不理解,必然肇始于对过去的无知”,似乎更该被我们铭记在心。同时,要想让每个人以各自方式置身其上的“生命存在的舞台”,也即各种各样的“房间”都具有(抑或可望具有)本应有的更符合人性需求的样貌,人们就确实没有任何理由完全“躺平”。至少就我个人而言,在阅读、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的确日益感觉到,既然有耄耋之年的佩罗及其近著摆在面前,本人虽年届花甲,也仍当继续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适时移译佩罗这样具有良知和担当的优秀史家的佳作亦是如此。
(本文系吕一民教授为即将出版的《私人生活空间史》所撰写的“译后记”,授权澎湃新闻首发,发布时有部分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