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再工业化进程需要中国的产业支持
近期,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提出,中美均受益于双边经贸关系。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两国企业和消费者通过双向贸易和投资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对美维系长期贸易顺差并非意味着美方是双边贸易的受损方。当前,需从中国出口贸易在维系美国社会经济稳定和再工业化进程中的建设性作用维度,看待美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受益关系问题。
美元霸权和贸易平衡是“鱼和熊掌”的问题
美国对外贸易平衡存在显著的技术悖论问题。对于一般贸易国而言,对外贸易失衡可通过汇率波动实现有效修复。市场机制下,本币汇率贬值能够通过进口抑制和出口促进实现贸易再平衡的有效调节。然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由于存在全球储备资产避险需求刚性,国际市场上长期存在其他货币对美元的“挤兑”,因而导致美元币值长期被高估,无法通过有效汇率调整的方式改善对外贸易平衡。
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于2024年11月撰写的《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提出上述类似观点。他认为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导致币值高估,进而使得制造业和贸易部门成本难以为继和美国对外贸易长期失衡。然而,维持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是美国寻求美元霸权的重要战略举措。布雷顿森林解体后,美国通过包括石油美元、国债市场和其他金融基础设施控制等手段维系美元霸权地位。美元霸权使得美元币值长期被高估。币值弹性缺乏导致其对于贸易平衡的调节能力大打折扣。这一技术性悖论导致美国无法同时获得货币霸权和贸易平衡。
中国对美出口顺差的本质是生产者福利的转移
通胀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隐忧。学术界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美国高通胀悄然而退仍存争议。在美国后续去产业化进程中,生产供给端收缩和货币发行同步增加的错位发展并未导致明显通胀。对于这一有违经济规律的反常现象,有必要在遵循大国经济互动发展规律基础上,从更具建设性的视角思考中国廉价进口商品对于平抑美国通胀压力的深远影响。米兰的报告在批评美元储备货币地位造成生产成本增长的同时,却忽视了其对于社会消费成本节约、通胀抑制和居民社会福利的深远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美国连续遭遇互联网泡沫和次贷危机,核心通胀率长期保持在2.0%-2.5%的低位。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报告显示,自1994年以来,从中国进口商品帮助美国年均降低1.3个百分点的核心通胀率。美国公司和家庭广为受益,1994年至2016年期间,美国消费者年均节省6230亿美元,占美国年均非石油消费支出的12%。换言之,若没有中国商品输入,美国2017年CPI数据将比既有水平高出27%,持续通胀累积将对美国社会经济稳定造成较大破坏。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本质上是中国生产者福利对美消费者的国际转移过程。由于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中低端产业“内卷式”恶性竞争越发严峻。中国生产者和美国消费者间的不对等议价关系使得处于需求方地位的美国采购商持续挤压中国生产者利润空间,最终形成对美国消费者的福利转移。比如,受上游采购者价格施压影响,沃尔玛中国供应商平均利润率仅为3%-5%,美国关税战甚至使得部分中国供应商长期亏本生产。然而,中国生产者福利挤出并未获得美方的客观看待,反而遭到美方苛刻的“补贴”和“倾销”质疑。
美国再工业化进程更加需要中国的产业支持
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去工业化”进程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颇感产业化危机,近年来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特朗普政府推出的高关税政策旨在通过抬升国外制成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为美国国内制造业发展腾挪空间。然而,高关税举措作为一种工业化初期的产业政策理念,很难适用于全球产业链分工时代。当前,美国无法通过保护主义方式完成所有中间品环节的国内生产,过时的保护主义举措无异于自毁工业化前程。
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具有梯度转移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当前全球范围内正进入工业化进程同步推进的时代。美国工业化进程将受到来自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成本竞争压力。全球产业链分工催生合作者关系变革,中间品供给的成本经济性和技术优势决定其工业制成品的市场竞争力。
面向未来,美国有效的再工业化进程需要采取更加务实的举措。中国拥有全产业门类优势,在关键中间品、新技术和新产业领域拥有显著竞争力。面对来自外部市场的剧烈竞争,来自中国的产业体系配套是最具经济性和竞争力的选择。中国理解美国对于再工业化的发展关切,也希望通过与美国重建产业和产能关系平衡,以寻求长远相处之道。
(作者王玉柱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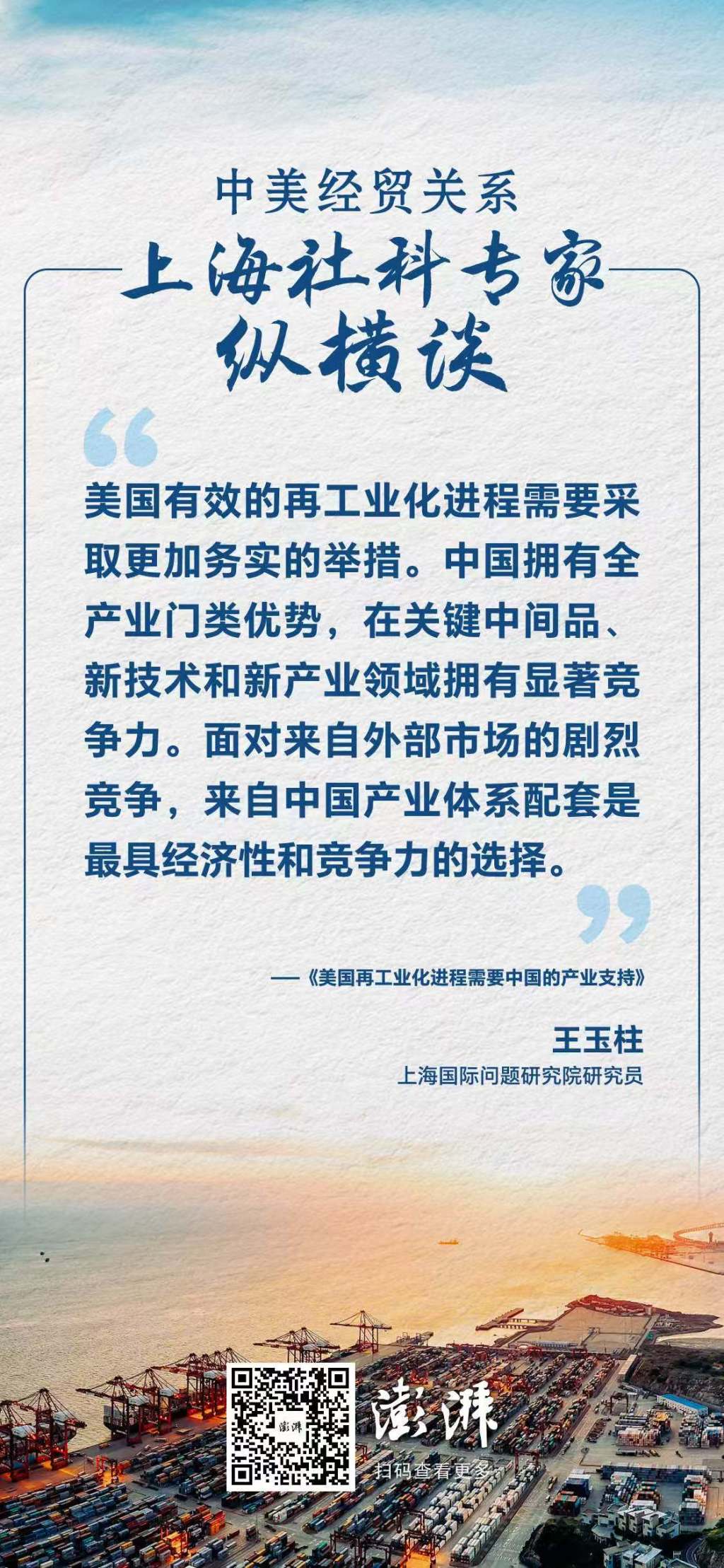
海报设计:白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