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内观冥想的历史漂流:从心理治疗室到“非语言现场”
印度佛教在历史传播过程中出现南北分裂,与北传中国、日本等地的大乘佛教不同,上座部佛教向南经由斯里兰卡传播,流行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南亚、东南亚地区,因此又称南传佛教。随着民族迁移、融合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成立,这一佛法地图被进一步复杂化。我在法国参加的Dhamma Vipassana课程,设置为高棉语-英语双语,是特为在欧洲的柬埔寨移民开设。这一文章将继续以我参加十天封闭课程的个人经历为起点,转向(或说跃向)一个更为当下、也更贴近个人的维度。长期以来,学界研究大多聚焦在白人中产阶级的灵性追求或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心理疗愈逻辑,而较少关注散布于欧美社会中的移民群体,如何重建自身的情感结构与社会位置。随着华人或亚裔群体从20世纪的政治难民、劳工移民逐渐转向为新一代的教育移民与经济移民,他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也从“生存焦虑”转向更为微妙的“归属、焦虑、自我调适”等心理议题。而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心理疗法,在面对移民的跨文化经验时,陷入文化贴近与误读的双重困境。在我看来,在这种语义堵塞与心理漂浮之间,冥想社区作为一种非语言性、去教义化、又能提供集体仪式感的实践,展现出跨文化群体探索精神安顿与文化连结途径的潜力。

一、跨文化情绪规训与心理治疗的局限
我与内观冥想的最初接触,源自我在欧洲高校就读博士期间一位亚洲同事的推荐。我们所在的区域研究所以亚洲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生中亚洲留学生的比例异常之高。这种结构本身,正是冷战以来西方“亚洲研究”体系的延续。一方面,它在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与身份政治兴起之后,主动吸纳亚洲背景的学者,以彰显多元化与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中,它也成为西方高校在学费制度与国际排名竞争中获取亚洲生源的重要节点。在这样一个同时受冷战知识结构与当代教育市场化逻辑双重塑造的空间里,亚洲学者既是知识对象,也被不断召唤为知识的生产者,既被想象为“研究者”,也常常被默认为某种“文化代表”。Sianne Ngai在《丑陋的情感》中指出,西方高校和文化机构中存在微妙的情绪审查机制,少数族裔必须在高校中呈现出“活泼感”(animateness)以满足对多元化代表的期待,以积极的、热情的、不过分理论、不过分批判的情绪形象增强自己的可视性和可被了解性。而当少数族裔表达诸如恼怒、冷淡等的负面情绪,则尤其容易招致“不理性”、“过度敏感”、“有敌意”的标签。因而,当这位亚洲同事与我分享他参加冥想实践以化解负面情绪时,这一“亚洲精神实践”在我们之间流转,并非仅是朋友间的文化话题,也是我们回应共同境况的一种情绪疗愈方式。
而对于我们这样的国际研究生而言,参加内观冥想营并不仅仅是“文化兴趣”或“宗教田野”的延伸,而更多出自对精神喘息空间的切实渴望。在高校体系中,博士培养制度常年存在结构性问题:高强度的个人研究压力、孤立的工作环境、不稳定的经济支持体系,以及“永远不够好”的自我评估体系,共同构成了许多博士生心理健康危机的诱因。已有研究指出,博士研究生的抑郁和焦虑症在全球范围普遍存在(Satinsky et al. 2021),而国际生面临的挑战则更为复杂。文化适应、签证与居留身份的不确定性、对母国与现居地之间的情感撕裂,使不少留学生长期处于一种被悬置的精神状态中。这一基础上,性别因素又进一步加剧了心理张力。2022年,墨尔本大学学者马嘉兰(Fran Martin)基于对数十位中国女性留学生在澳生活经历的五年民族志研究,出版了专著《远走高飞之梦:中国女性留学生在西方》(Dreams of Flight: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Students in the West)。她指出,对于许多中国女性来说,出国留学不仅是获取知识和学位的过程,更是一个通过“离家”实践自我主体性的旅程。然而,这种自我探索常常被现实层面的孤独、漂泊感、家庭期望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所压迫,形成一种隐秘的心理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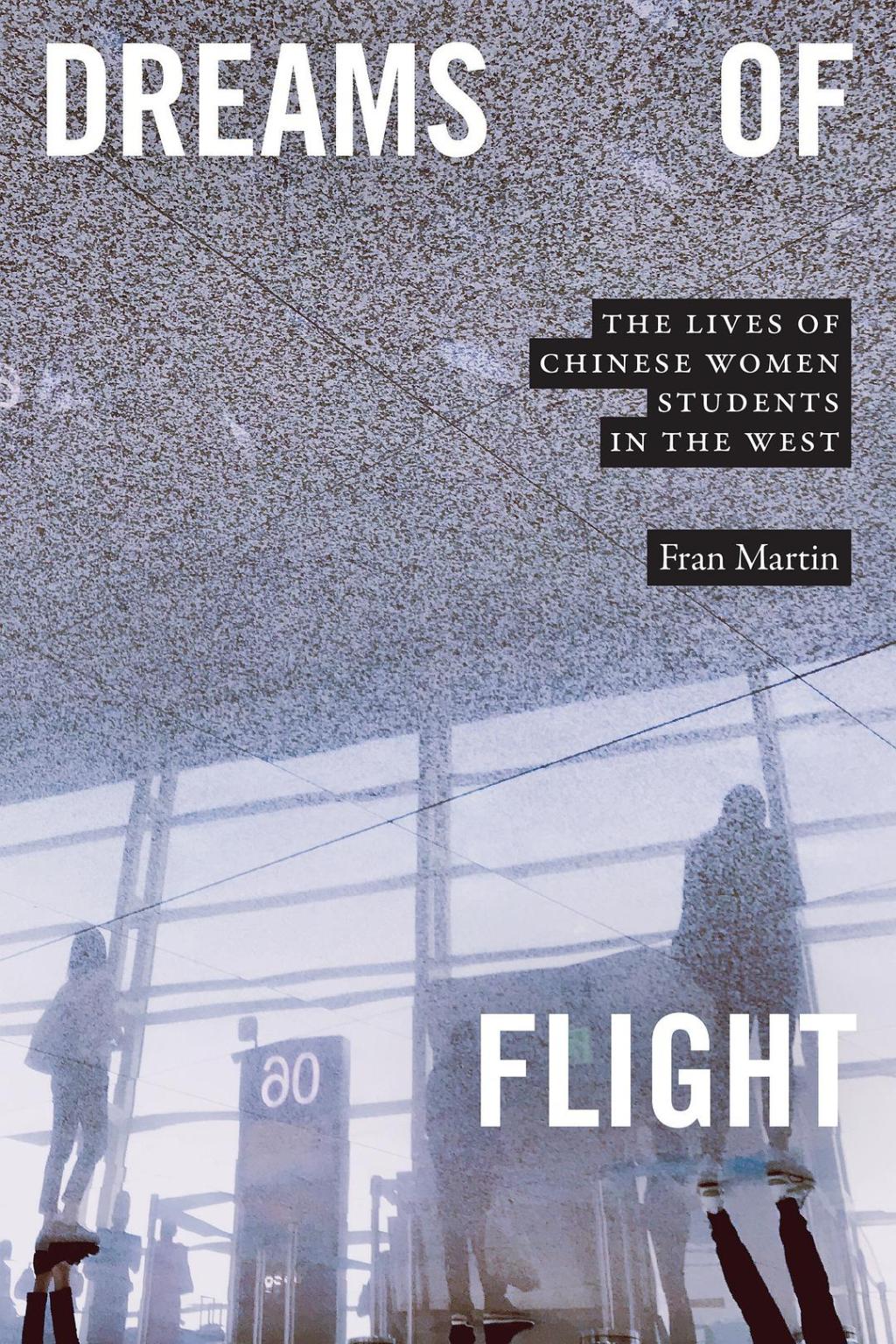
这种隐秘的心理张力,最终极有可能具体现形于心理咨询疗程中对于“文化贴近”的努力。在我个人经历中,大学医院主动提议安排一位中国籍女性心理咨询师,体现出机构对于语言、文化背景、性别经验的敏感考量,试图通过“相似性”降低治疗过程中的异质感与情绪阻抗。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我深知,海外华人学生之间高度重叠的私密网络,使得这种文化贴近的配置反而意味着更高的暴露风险。在移民社群(本文将广义上的“移民群体”扩展至包括那些在跨国教育体制中流动的国际学生,尤其是长期处于迁移状态、面临归属断裂与身份错位困境的亚裔留学生。他们虽未被传统意义上归类为移民,却同样处于语言、文化与社会结构的边缘之中)的交错社交图谱中,“专业帮助”常常并不意味着“安全距离”。而“谁有资格知道我最深的痛苦”、“我愿意对谁暴露我的脆弱”,是关于身份信任的微妙情感政治。最终,我得到了一位希腊裔、坐轮椅的男医生。然而,距离的安全,也意味着一种持续的间离。近年来,跨文化治疗关系中的“文化适应性干预措施”与“治疗师的多元文化能力”,已成为心理治疗学界的重要议题。然而在我的体验中,这种“文化敏感”有时也可能演变为一种善意的、刻板的预设理解。作为一个“亚洲女性”“中国学生”“远离故土的留学生”,天然地承载着某种特定的情绪模板、家庭结构或文化编码。于是,我所讲述的困惑与焦虑,往往会被迅速导向“文化归因”的框架之中,例如“你可能不容易表达负面情绪,是因为儒家文化强调克制”,“你对于成就的焦虑,可能源自东亚家庭对子女的高期望”等等。这些话可能并不全然错误,但它们让我感到一种被动,似乎我在配合一个既定的文化剧本。这种以“理解”为名的归类,反而遮蔽了那些更为复杂、游移、不易归类的经验。原本意在“贴近”的文化适配,最终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难以言明的距离。
呼应伊娃·易洛思关于“心理化”的观点,情感困境在制度与语言中被标准化为“可以管理的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在跨文化心理治疗的实践中,移民背景常被视为一种需要调适的特殊性,其复杂经验被简化为可归因、可介入的心理议题,治疗的目标不再是深入理解,而更倾向于引导个体顺利融入并适应西方社会的行为与情绪规范。2023年夏天我在国内进行田野调查,咨询转为线上,我在流动中的各种角落(餐厅外、星巴克、酒店房间甚至是在高铁火车厢接驳处)用英语小声与他交谈。这些场景拼贴构成一种“怪异的”(unheimlich,该词翻译问题十分复杂,在此不做赘述,此文使用兼取“无家可归般的不安状态”和“介于熟悉与陌生之间的”两意)体验,我身处被他归因为“压力来源”的“家国”,用一套来自另一种社会语境的概念系统,试图对我生活的意义与苦恼进行命名。语言异质感、空间错位感以及“被解读”经验中的异化,使我感到双重的漂浮:一方面是我个人空间的移动,另一方面是语言的——我被迫在自己的母语世界中,以一套翻译后的概念,解释一种本应由自己经验命名的情绪。这种“被理解”的过程,并非暴力,却令人疲惫。我忍不住想,这场由欧洲高福利国家医保系统全额报销的线上心理咨询,到底是某种有效的心理照护,还是第一世界中产阶级的精致自恋?甚至,我对“归属”“自我”“界限”的焦虑,到底是结构性的精神困境,还是资源过剩后的精神矫情?“你值得被听见”、“你可以拥有空间”这样的对话模板,它们是心理疗愈的万灵药,还是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安全的回应?
二、非语言现场中个体的重逢
在某种程度上,Dahmma Vipassana通过封闭营地、高强度静坐冥思、全程禁言而达到的非反应性、非语言性的实践,确实为参与者提供了从知识社会结构中暂时解脱的机会。参与者不必说话、不必解释、不必被翻译,也不需要回应谁的关切。在葛印卡的教导体系中,冥想并非对意义或情绪的认知诠释,而是一种严格训练自我意识回归身体的练习。他反复强调:唯有通过对身体感受(bodily sensations)的持续觉察,个体才有可能脱离语言与概念所构筑的认知路径,打破对过往经验的情绪回路,逐渐“烧尽”潜伏于潜意识中的“业习”( sankhāra,或译“心理反应模式”)。所谓 “业习”,并不单指我们有意识中的情绪或想法,而是那些深植于身心层面、自动发生的反应性结构。一个人一旦掉入“贪嗔痴”的惯性循环中,这些反应就会不断累积,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支配情绪、决定判断、塑造命运。
如果将“业习”与弗洛伊德对无意识与重复性强迫的分析进行对读,会呈现出饶有趣味的联系性。两者虽然立足于不同的哲学传统,却都试图解释一种超出意识控制、深植于身体与习惯的反应机制。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指出,主体常常不由自主地重复创伤经验,并非出于快感,而是因为潜意识中尚未被“通过”的冲突需要借助重复来寻求象征性的解决。因此在弗洛伊德的设想中,疗愈的前提是“说出”(Durcharbeiten),即患者需在治疗者的引导下,将那些潜伏在潜意识中的冲突、欲望与创伤通过语言表达的方式逐步意识化,从而削弱它们对行为与情绪的无意识操控。这是一种相信主体有能力“讲述自我历史”的路径。语言在此被视为通往内在真相的桥梁,治疗者的工作则是成为那个“聆听并赋予解释的人”,将原本混乱、重复、痛苦的体验纳入一个可以被命名、整理、再编码的语义秩序。然而,这样的路径也存在其内在悖论。它高度依赖语言的能力,也依赖说者对自身历史与情绪有“可叙述性”的预设。而当说者身处移民处境、跨语言语境,甚至文化无法互译的边界时,这一体系的局限性便逐渐浮现。正是在这种语义卡顿之处,内观静修的非语言性实践,才显现出它作为另一种“疗愈形式”的可能性——一种不诉诸解释、不诉诸理解,仅通过身体与感受的直接经验进行的“沉默的工作”。对葛印卡来说,冥想的目标不是“理解”这些结构,而是通过非反应的身体觉察,把它们一点一点“看穿”并“熄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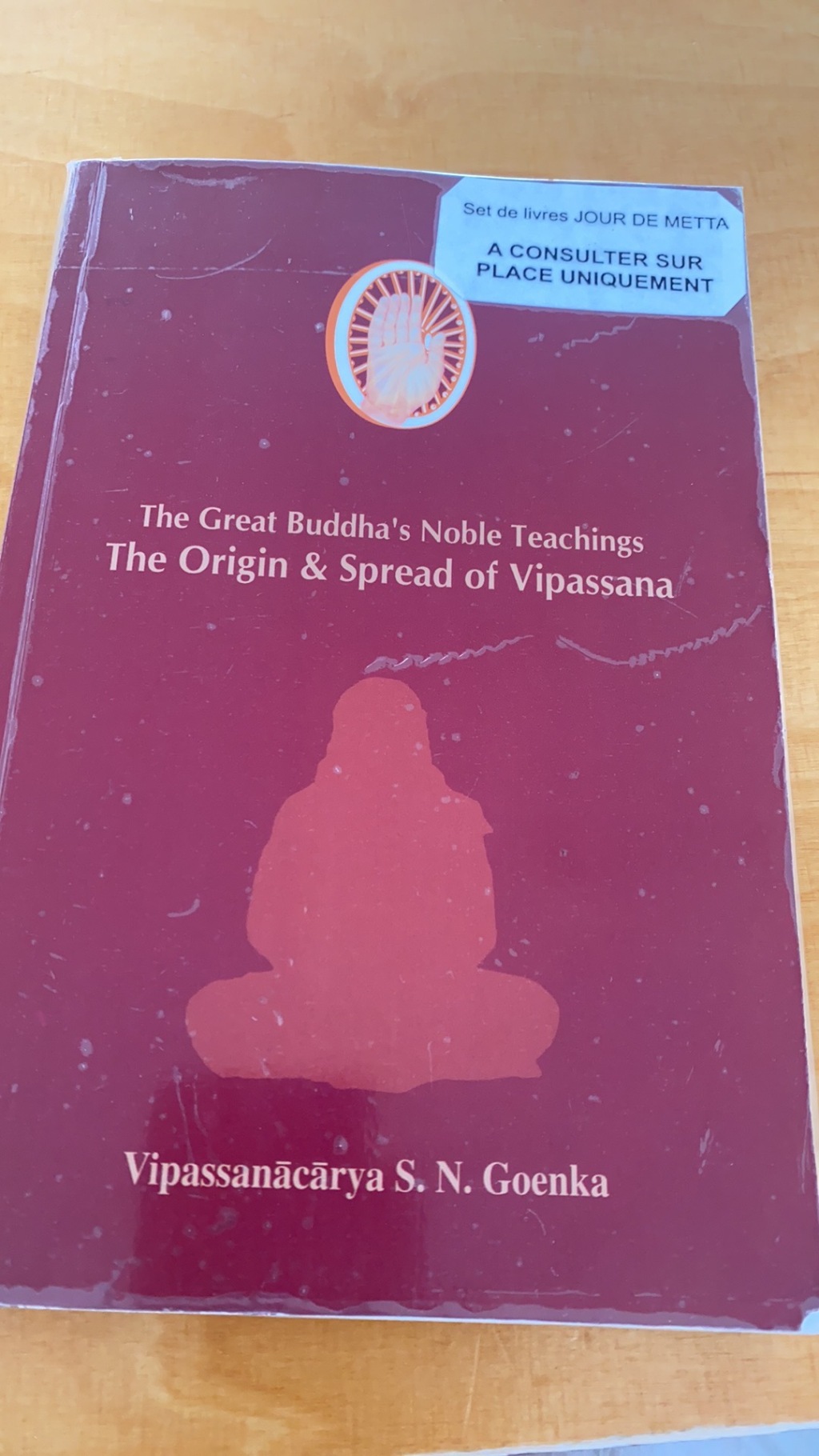
中心收藏的资料书籍
Dhamma Vipassana的课程简介将内观冥想定义为一种精神净化的方法,旨在帮助实践者以平静、安定的态度应对生活中的紧张与困境。然而,要掌握这一方法并不容易。因此,营地要求学员必须遵守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以高强度练习支撑技法的深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开始首轮两小时冥想,除早餐、午餐和晚茶的短暂休息外,全天累计冥想时间超十小时。在这样的高强度冥想中,除了与自己的困意作斗争,还需与“思维漫游”这一人类古老习惯周旋。我个人经验是,当思维在记忆碎片中跳跃时,潜意识深处被压抑的冲突、欲望与创伤也随之自然浮现。依照葛印卡的教导,面对这些记忆,面对这些从潜意识上涌的记忆与情绪波动,学员应将意识温和而坚定地拉回至对身体感知的觉察(sati),在反复实践中逐渐培养 “不喜不悲”(upekkha)的中立态度。十天的退隐有效地将自我与日常生活的外界刺激中隔离开来,使我得以完全沉浸于自我精神世界的探索。在最初的几天,我仍然频繁因记忆的刺激而产生情绪波动,这种波动在第四、五天达到顶峰。自第六天起,我开始感到某种转变,我与记忆之间拉开了微妙的距离,它不再即刻牵引我的情绪,我能以一种更为冷静、观照的态度面对它带给我的震荡。当然,我必须承认自己并未做到葛印卡所提到的“仅仅观察而不介入”,面对某些深层的记忆与情绪,意识仍不自觉地生起评判。即便如此,在持续练习中产生的微小松动,仍然让我体会到“保持觉知而不反应”的可能性,一种经由身体感知层面逐步习得的、微弱而真实自由感。回归日常生活后,我察觉到自我对过去易引发烦躁或者愤怒的食物,反应变得稍微平静。冥想并未消除情绪,但能帮助我在情绪波动中保持觉知,以更中立的姿态观察、反思和抉择。
但对于我而言,这次行程更重要的,并非自我观照,而是一次完全未曾预期的人与人的相遇——上一代的亚裔离散者群体,与我这样东亚新一代的留学生,在这片法国郊外的树林中,意外形成了一种时空交汇的局面。我参加的课程为高棉语-英语双语课程,两位主讲教师皆为柬埔寨裔,主要以高棉语授课。英语学员,连我在内,仅占不到三分之一。第一天抵达营地时,我看到许多亚裔中高龄,他们集体驱车而来,把后车厢里满满当当的捐赠食物搬进厨房,彼此之间熟稔地用高棉语打招呼,站在营地前院聊天,一派悠然自得的“常客”姿态。我意识到他们是这个现代佛教网络中的“原住者”,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一次偶然的“灵性之旅”,而是早已纳入生活节律的精神实践地。虽然语言不通,但她们的举止、笑声与穿着中,给予我一种熟悉的气质——那种属于东亚社会母亲、阿姨、邻居辈的身影。她们不像我这样小心翼翼地观察规矩、紧张地准备“入定”,而是自然地从世俗族群的社交状态过渡到自我灵修。
在十日禁言期间,当偶然对视时,我能察觉到她们眼神中的善意和识别。那是一种不需言语的凝视,她们知道我是中国人,而我推测,我在她们眼中不是陌生的异族“禅修者”,而是某种更近的“自己人”。这种目光中的识别,并非抹除族裔差异,而是在差异之上生成的一种微妙亲近。这并非某种“超越性”的灵魂邂逅,反而是非语言符号构成了足够复杂的识别边界,才使这段禁言中的相遇产生出短暂联结。语言并非唯一的意义生成方式,我们与他人“共在”(Mitsein)于这个世界,在语言之前,已经共享一种结构性经验。具体而言,识别、接纳、归属这些核心经验,并非靠语言,而是通过肢体、面部、共时的空间得以传达。因此,沉默并不是语言的缺失,而是另一种意义厚度的延展。这种沉默中的确认,不是天然的,也非超越性的,反而是在差异高度可见(种族、年龄、课程语言、着装)现实中发生的某种情感交汇,是植根于共同移民经验、族裔记忆与女性身体的真实连结。
禁言解开当日,语言再次成为个体建立联系的媒介。几位阿姨和奶奶用法语试探地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不会法语,她们随即改用粤语。在一个以法语为主、高棉语为次的社群空间中,粤语这门“边缘语言”忽然成为我们之间最自然的通道。我这才知道,她们大多数是柬埔寨华侨,1975年从金边逃亡,经由泰国难民营辗转抵达法国。如今,他们在法国已有一个相当大的侨民社群,家庭、亲戚、朋友之间定期一起报名参加禅修课程。由于缺乏系统性的访谈调查,我很难做出更进一步的“解读”。但在我有限的观察中,她们在法国制度化禅修系统中形成了极强的在地适应力和文化主体性。移民经验、禅修实践与代际传承交织出一个扎根于法国、延续着东南亚佛教记忆的“生活共同体”。巧的是,Dhamma Vipassana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向西方的传播过程中,在欧洲首先落地法国。在我的浪漫化想象中,这甚至可以被视作一种对西方私人化、心理化灵性消费的主动重夺(reclamation)。Dhamma Vipassana 以非营利结构维系,它的制度性与非商业化,为这类在地移民社群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可能。这些离散群体并非被动融入全球冥想网络的“他者”,而是在制度化禅修体系中重新定义了冥想的社会位置与集体功能。禅修营因此不再只是个体灵性修炼之所,也是在离散群体从战争、迁移到重构在地社区的“再疆域化”过程中,延续归属、重塑秩序、维系意义的“精神基础设施”(spiritual infrastructure)。
尾声
当然, 这一切论述和理论想象也可以被视作为我这样一个人文学者惯常的意义游戏。在一个具体而微的个人故事面前,所有我曾试图调用的宏观历史和概念术语,都显得遥远且离地,是知识世界中的再生产。一位柬华裔阿姨和我讲述她的故事,她6岁便和家人离开金边“走难”,能说非常流利地道的法语、粤语、闽南语以及高棉语。结营那天,告示板贴出结营公告,她悄悄地来问我上面写了什么,附耳告诉我她并没有上过学,所以完全不识字。这是她第二次来冥想营,修行诉求是收敛自己过多、过急的口头表达。我偶然投入这一“非语言现场”,在沉默、静坐与群体之间,或许也应该学会“不语”。最后,我希望用每次内观冥想课程结束时,葛印卡和学生的对话仪式来结束文章。
Bhavatu sabba maṅgalaṃ (愿一切吉祥安好)
Sadhu Sadhu Sadhu (善哉 善哉 善哉)
参考文献:
Fran Martin. Dreams of Flight: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Students in the West.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2
Eva Illouz, Saving the Modern Soul: Therapy, Emotions, and the Culture of Self-Hel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Ngai, Sianne. Ugly Feelin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Thomas G. Kirsch, Spiritual Infrastructures. In Rethinking Infrastructure Across the Humanities. Pinnix, A et cl ed. Bielefeld: transcript, 2023, pp. 155-161.
Sigmund 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rans. J. Strachey. The Hogarth Press. 1955.Satinsky EN, Kimura T, Kiang MV, Abebe R, Cunningham S, Lee H, Lin X, Liu CH, Rudan I, Sen S, Tomlinson M, Yaver M, Tsai AC.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Ph.D. students. Sci Rep. 2021 Jul 13;11(1):14370.